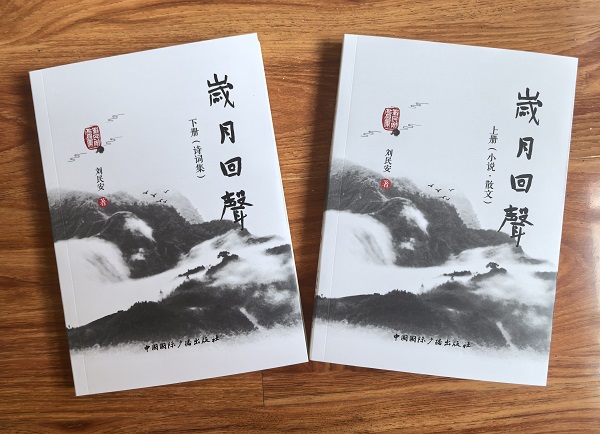在大雁塔的晨钟与洛阳城的暮鼓之间,在秦岭的云影与邙山的烟岚深处,诗人孙香芹以三十年时光雕刻着属于自己的诗歌版图。这位从洛水之畔迁徙至长安城下的"爱心诗人",用《孤帆远影》的漂泊与《踏歌长安诗里行》的笃定,在古老的长安里种下月光,在留守儿童的笑容中留下温暖。
孙香芹在我的心目中,她不是被文字简单定义的 “女诗人”,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的诗人,我认为,她是长安城里笔尖流转星光的女诗人,是站立在古老城墙之上最有才气的女诗人。
我想,我们应该走进这位我们都熟悉的长安女子,走进她的诗歌,更走进她的内心世界。
我与诗人孙香芹相识是在十二年前,我正在甘肃庆阳市某一高中读书,那时是全民QQ的网络世界,还没有微信,我们的交流仅在QQ上面。由于我还要上学,也很少看QQ,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文学的交流群里看到一个名叫“孤灯”的诗人发在群里的诗歌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虽然我在高中的时候并没有开始文学的创作,由于我作文写得好的缘故,也喜欢读一些课外书,在QQ上面加的读书、文学的交流群也多,时常也会在群里互动,与其说是互动,倒不如说是在群里潜水,学习各位老师们的作品与读书的心得。就是这次偶然的机会,我也冒然的加了这位诗人的QQ,由于我还是学生的缘故,说起话来也小心翼翼,但是“孤灯”老师是那么的直爽、开朗,知识面又很广,对读书、文学又有着独到的见解,这是我们认识聊天的第一印象。
其实,当时在我的心中,已经成为我的老师。在以往后的时间里,孙香芹老师便于我畅谈文学、诗歌,在一定意义上让我更加喜欢上了文学与诗歌的创作,直到今日,与孙香芹老师相识十二年,我参加工作八年了,也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热爱,这也来来源于孙香芹老师的鼓励与支持。我们亲切的称为“四姑”,我始终心怀深深的感恩。在我追寻文学梦想的道路上,她给予了我太多无私的帮助,那些温暖的扶持与指引,至今想来仍让我满心感激。
今天,我想以一个九零后的诗歌写作者,谈一谈诗人孙香芹的诗歌,这也是我的一些浅薄的想法。
我会从四个角度去刨析诗人孙香芹的诗歌作品,也可以说这四个角度是相互重叠的精神维度,具体是那四个角度,分别是:
长安,诗人从地理栖居到文化扎根;
亲情,以诗为小舟,横度死亡的河流;
爱心,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;
故乡,作为异乡游子重构的精神原乡。
这四重相互重叠的维度则是交织着她诗歌的复调,也是折射出现代一位女诗人精神的一面镜子。
一、长安:诗人从地理栖居到文化扎根
十九岁那年,孙香芹义无反顾地背起行囊,坐上绿皮火车从洛阳奔赴长安,而这座历史文化古城,从此成为她人生的第二生命。
在诗歌《长安颂》里,她写道:"我的长安——我爱你/我要把灵魂嫁给你/千年都城的魅力/唐风汉韵润心雨/一块块秦砖与汉瓦/讲述着五千年的文明与昌盛/记载着你千秋的足迹",诗人以炽热的情感锚定长安的精神坐标,“灵魂嫁给你” 的热烈告白,将个体生命与千年都城结合在一起,形成文化共同体。在诗人孙香芹的心中,长安不仅仅是地理空间,更是成为了诗人灵魂皈依的文化原乡。
诗歌《回望长安》,她写道:“大雁塔和钟楼屹立在城墙内外/古老的大神州从远古走来/携一幅人间春秋在天地间铺开画卷/大长安的儿女纵情高歌/挥笔续写下天地传奇。”诗人以具体意象为锚点,在历史追溯与个人情感中生长出多层的情感肌理,既藏着对故土的眷恋,又透露着对文明传承的担当。诗人不把故土当 “标本”,不把历史当 “影子”,而是将长安、神州、人间春秋都视作自己情感的生命体。她的追溯里没有怅惘,只有确认,她的歌颂里没有浮夸,只有认领。
诗人孙香芹曾作为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分会的策划者与执行者,她深谙"长安"二字的文化重量,在《长安女子》诗中,她以凝练的笔触勾勒出长安女子的精神群像,将"婉约与豪放"的笔墨融入汉唐文脉的时空里。诗中“用书香熏陶女人的魂/文字留下永恒的美”的意象,让我们感觉到,长安女子从唐风汉韵中款步走来,她们用文字镌刻的不仅是四季风景,人间烟火,更是文化传承中永恒的精神芳华。
诗人孙香芹诗歌中的长安意象,从来不是孤立的意象符号,而是她情感的 “具象化载体”——我们可以这样理解,在诗人孙香芹对长安的书写中,意象是诗人情感的 “锚点”,情感是诗歌意象的 “灵魂”,二者相互融合,共同构建起她与长安从 “地理联系” 到 “精神共存”,再到“灵魂相依” 的深层次关系。
也可以这样说,诗人孙香芹诗歌中的“长安意象”,是她情感表达的 “外化镜像”,因为她的诗歌意象中所出现的“大雁塔”“长安”“感业寺”“武则天”是对历史承载的回望,我可以称之为“历史意象”。而“历史意象”也承载她对长安文化根脉的敬畏与归属;而她的情感,又让这些意象脱离了 “历史标本” 的刻板,成为 “有温度的生命体”——就像她把长安视作 “第二生命”,“历史意象”是她与长安 “精神共存” 的纽带,让她的情感有了归宿,也让长安的意象因她的书写有了更鲜活的灵魂。
二、亲情:以诗为小舟,横度死亡的河流
我想,每一个经历寒冬的人自然是不能忘记慢慢暗夜及其投射的阴影。诗人孙香芹就是经历过这样寒冬的人,才能写出令人潸然泪下的抒情诗。诗人孙香芹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感受力,她能抓住生活中那些细微,容易被忽略的东西,用深邃的思想写出感化心灵与读者共鸣的好作品。
亲情,在孙香芹的诗歌中占有重要的比例,却从不是直白的 “思念” 或 “感恩”。
她在《天堂里的父亲》中的情感是如此的真诚又热烈,“多少次从异乡的梦里哭醒/望着窗外的星空/我知道这一次您真的走远/我知道父亲您再也不会回来”。“异乡的梦” 是她诗歌里常见的情感容器。异乡的漂泊感本就带着孤独的色彩,而 “哭醒” 是最个人的生理反应 —— 没有修饰,没有比喻,此处的直白恰恰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。最令我动容的是两个 “我知道” 的重复。这不是呐喊式的热烈,而是一种清醒的、带着痛苦的反问。第一个 “知道” 是理智上的接受(“真的走远”),第二个 “知道” 是情感上的撞碎(“再也不会回来”)。这种热烈里没有一丝夸张,全是 “不得不接受” 的真实 。
在此处,我与诗人孙香芹有着相似的经历,就是我祖母的去世,也是让异乡的我从梦里哭醒,我们都深刻的体会到,每个失去亲人的人都懂的那种,在某个寻常的凌晨,突然被现实砸中胸口的、带着寒意的疼。
她在《母亲的爱》中情感是如此的细致与温暖,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的恰到好处,“母爱如山/心里装满着对儿女的思念/母爱是雨中的小花伞/陪我走过了风雨童年/母爱是煤油灯下纺花车的线/母爱是我脚上的老棉鞋/一针针一线线/包含着母亲最深的爱。”对这一首的创作来说,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抒情诗,这首诗流动着诗人的血液,这种对母亲情感的表达是如此的真切、生动、细腻、充沛,这种情感的表现更能唤起与读者的共鸣。
其实,诗人孙香芹的情感很少是单一的,亲情与长安的情感、乡愁与归属感,总通过意象交织在一起,形成更复杂的情感肌理。
沈德潜的《说诗晬语》所讲:“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,难矣”。那么,诗人孙香芹通过对亲情的本真描写,将个人的悲痛升华为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。这种“不回避情绪的真诚”,恰如沈德潜所言“诗贵性情,亦须论法”——她的诗歌实践也证明,传统诗教的核心不在于形式上的复刻,而在于对情感深度的挖掘。
三、爱心: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
诗人孙香芹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“爱心诗人”,先是将“爱心”放在前面,“诗人”放在最后,这一点,读者或许很难理解,为什么是“爱心诗人”而不是“诗人”呢,其实,当我们走进诗人孙香芹的人生轨迹里,她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公益人,为此,她也写下大量的诗歌作品。
在《大爱如山》里,她记录了山区孩子的求知的信念:“望着孩子求知的双眼/又有谁舍得离开”,诗人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深沉的情感与精神内核,这种在具象场景中自然流露,极具感染力。
在《孩子,请不要把自己当大款》中:“孩子,请不要把自己当大款/大手大脚挥霍着父母的钱/任意挥洒挥金如土/你可知道父母挣钱的艰难”,这种对孩子现代消费观的告诫,传递着正确的价值观。这直白的言语更能击穿读者的心灵,还有对孩子不知父母在外拼搏幸苦的劝慰。
所以,诗歌的价值从不限于辞藻的华丽,当它直面生活里的真实困惑,用最朴素的语言打通情感通道时,反而更有穿透性。诗人没有用隐喻、象征等诗性技巧的修饰,却以近乎日常对话的直白,直观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。
据我所知,诗人孙香芹还是西安市一家“星星家园”的名誉园长,星星家园长期收留残障儿童,而她本人始终将目光始终投向这些需要被看见的群体,常牵头组织慰问活动,用温暖的行动为他们送去切实的关怀。
诗人孙香芹为此也创作了部分的诗歌,她的实践证明,真正的公益写作不是道德说教的传声筒,而是以审美之光照亮生命的火炬。她用诗歌为残障儿童构筑起精神栖居之所,这种创作与公益的深度融合,为当代诗歌如何介入社会提供了可能性。
与此同时,诗人孙香芹对老兵这一群体也是比较的关注,在《老兵》中:“今天的幸福/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/问候一声老兵/我亲爱的兄弟/国家和人民会永远感谢您”。诗人从不用华丽辞藻的语言去表达,只用最朴素的语言,让被关注者感受到 “被看见” 的温暖。就像这几句诗,这正是朴素诗歌最动人的力量。
诗歌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,而拿这个镜子的人就是我们的诗人,诗人孙香芹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,这是弥足珍贵的,现在很多诗人是丢失了初心的,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,无论是作家还是诗人,我们的创作都要面向于社会的底层,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,永远用一颗善良的心创作,那么诗人孙香芹这在一方面是非常合格的,她诗歌最具有穿透力的,时刻体现着人文主义的光芒。
四、故乡:作为异乡游子重构的精神原乡。
洛阳始终是诗人孙香芹永远的诗源。
在《故乡的那片金黄》中,她写道:“多年前那个怀揣梦想的神都女子/从旷野之上大地的前方/脚步随蓝天白云去了遥远的远方/故乡啊!我的故乡/你是否知道/我怀着前世今生的惆怅/蹉跎在时光的倒影里/我魂牵梦绕的乡愁/在长安的风中流浪,流浪”。诗人孙香芹把“乡愁”从抽象的情绪,变成了可感知的 “生命状态”,很多诗人在写“乡愁”时,是被蒙上了一层面纱,这样的面纱让读者变得有了陌生感。而诗人孙香芹的表达是没有这层的面纱,为读者解开了这层面纱的神秘,让读者亲切的感受到这就是“乡愁”。
我们知道,时间的流逝会在我们每个人留下 “蹉跎”的痕迹,但是永远消磨不掉对故乡的牵挂。那么,诗人最终所有的意象都指向一个核心,那就是故乡是 “出发的原点”,也是 “永远的终点”,而漂泊的意义,就藏在 “魂牵梦绕” 的追忆与回望中。
诗人孙香芹在《孤帆远影》(后记)写道“没有经历过的人,永远也体会不到内心的孤独与恐惧,冷静下来后才发现不能沉沦,不能让自己变成尘埃。走出围城的我一无所有,一切归零,像城市里无根的浮萍,又开始了艰难的漂泊”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写照,这让我想起她写过 “十九岁奔赴长安时的绿皮火车”,那时的漂泊带着憧憬,带着美好,带着信念,而此刻的漂泊带着 “归零” 的沉重 —— 但恰是这种沉重,让 “重新开始”才有了力量。
当诗人背起行囊离开故乡的时候,很清楚自己想去哪里,那就是长安,长安是诗人梦中的精神家园,是诗人灵魂的归处。
诗人在《长安秋月光》中写道:“剪一缕月光入睡/枕着那似水的光辉/让我在梦中回归/故乡的风景最美/剪一缕长安秋月/让故乡在月色里入梦/洛浦杨柳依依/龙门石窟伟雄/伊水洛河神龟/童年在神话里陶醉,/剪一缕月光入睡/让故乡再梦里约会。”,我们知道,诗人孙香芹的故乡在洛阳,但是诗人带着洛阳的根活在长安,又让长安的月光,成了故乡在她生命里的另一种存在。而“月光”恰恰是两座古老城市的 “联络官”,洛阳是 “出发的原乡”,长安是 “落脚的当下”,而诗人内心的牵挂不是撕扯,而是让故乡的魂借着长安的月色安身,让长安的夜晚因装着洛阳的梦而温暖。
诗人孙香芹对故乡的重构,在《轻轻地走过故乡》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诗中的“村庄”既是真实的洛水地标,又是家族记忆的载体。“乡愁被连根拔断/故乡的一草一木/失去了一片云天/轻轻地/走过我梦中的小村庄/心中留下无尽的忧伤。”诗人想抓住“有云天、有根” 的故乡,可现实里只剩下“断了根、失了云天” 的轮廓,这里的 “故乡重构”,是诗人记忆与现实碰撞后留下的残影。诗人把最沉重的痛苦,藏进最轻的诗句里,让故乡的重量落在每个 “想回却回不去” 的瞬间里。
这是我从四个方面对诗人孙香芹诗歌简单的阐述,无论是在洛阳还是在长安,诗人孙香芹都会用诗歌搭建着自己精神的广厦千万间。她的故乡洛阳是诗人生长着爱与疼痛的活体;她的亲情是以诗为小舟,横渡死亡的河流;她的爱心是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;她的故乡是异乡游子重构的精神原乡。
当我们在《孤帆远影》中看见那个"背着诗歌流浪的长安女子",会突然懂得:真正的诗人,从来都是用生命在写作——那些公益路上的脚印,那些留守儿童的笑脸,那些深夜痛哭的诗行,最终都化作了照亮时代的星光。
当我站在2025年的夏夜里回望,诗人孙香芹的诗歌轨迹,从洛阳到长安,从个人到众生,从伤痛到慈悲。她用三十年时间证明,当诗歌扎根于大地时,当爱心化作文字的锋芒,那些被生活折磨的灵魂,终将在诗行中舒展成翅膀去翱翔。这或许就是诗人孙香芹最深刻的感悟——她的每一首诗,写给长安,写给母亲,写给所有在异乡中艰难跋涉的人。
作者简介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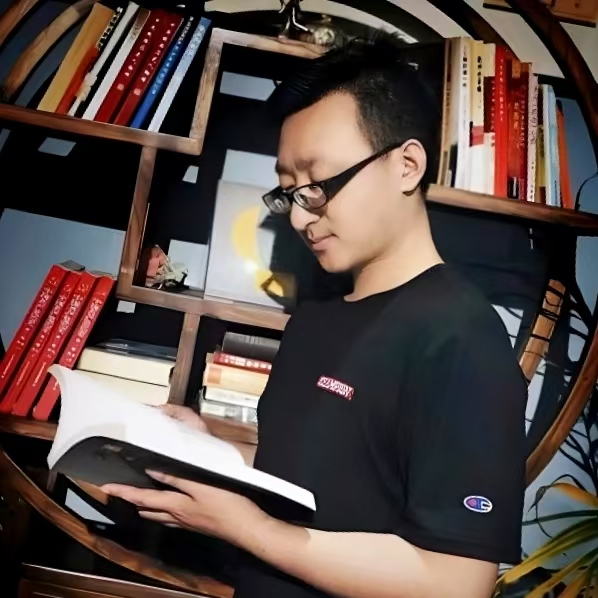
王鹏飞,笔名小麦子,九四年出生,甘肃环县人氏。现定居西安,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为陕西大唐文化艺术社副社长、主编。作品散见《美文》《长安诗刊》《雁塔文艺界》《环江》《中诗报》等。
↓下一篇:最后一篇